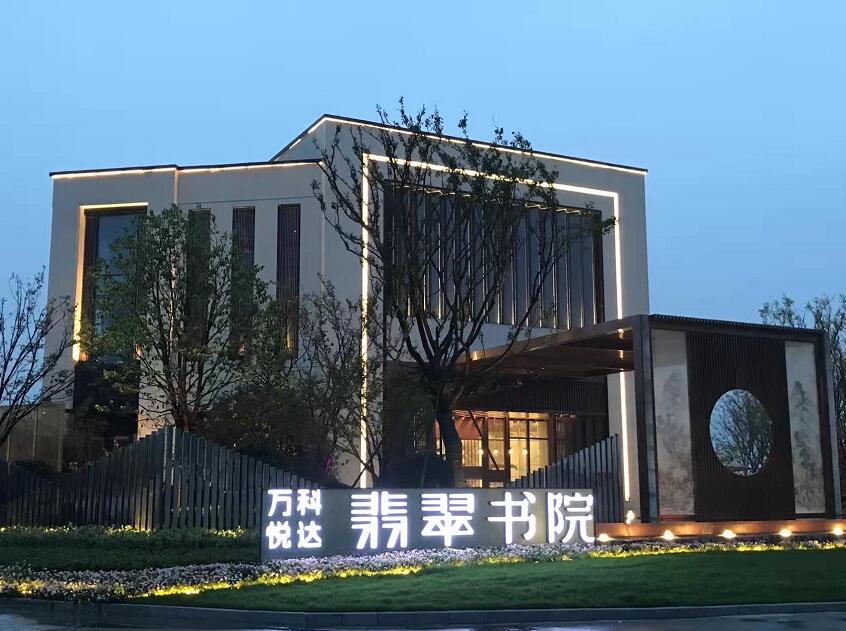它們可能�5嚴實實。
它們可(kě)能貼在樹上(shàng)、房簷,甚至(zhì)你家大門上。泛濫時,過街天橋的階梯上,一腳下去是重疊四五層的小廣告。還(hái)有膽大的,在警車、城管車,還(hái)有康熙年間(jiān)的文物(wù)上(shàng)都留下了(le)小廣告的印記(jì)。
習(xí)慣了(le)基地裏整齊的紅磚樓房,裴延印夫婦接受不了“亂糟糟”的(de)北京(jīng)。接受(shòu)了30多年的軍(jun1)事化管理,做衛生早已成為習慣(guàn)。老兩口(kǒu)決定用小鏟(chǎn)對(duì)抗這些(xiē)小廣告,也算是打發(fā)退休生(shēng)活。
早晨6點到9點(diǎn),下午4點到7點。幾乎是固定的時間,他們(men)會牽起小狗“毛毛”出現在家附近的街頭巷尾。時間久了,“毛毛”有時候看見地上的小廣告也會(huì)用爪子(zǐ)扒拉。
這些(xiē)年,小廣告的黏性越來越大,貼得也越(yuè)來越(yuè)高。裴延印把裁紙刀(dāo)片纏上(shàng)硬紙板,再用透明膠捆好。刀(dāo)片經常刮壞,家裏就(jiù)放十(shí)多把(bǎ)備著。他(tā)還把可伸縮的拖把杆卸了,改裝成1.5m的(de)長鏟。
最(zuì)難弄的是貼在地上的小廣告。人的(de)重量加上膠水的(de)粘合,來回踩過千百次(cì)後,薄薄的(de)一張紙(zhǐ)就像是和地麵長(zhǎng)在(zài)了一起。有一次,裴延印把(bǎ)指甲摳劈了,血肉模糊(hú)。一年後,灰突突的新指甲頂出皮膚,從此他(tā)揭小廣告時總會戴上手套。
想盡辦法的不止他們,麵對著被刮花的玻璃和布(bù)滿傷疤的鐵(tiě)器(qì),環衛和城管用上了高壓水槍、高端樹脂霧化專業(yè)城市清潔機、能(néng)把鋼鐵打得鋥亮的水砂槍,以及專門為胡同小(xiǎo)巷設計的(de)小(xiǎo)三(sān)輪蒸汽清洗車……
2007年,北京曾推出《各類市政設施(shī)防護性(xìng)塗刷規(guī)範(試(shì)行)》,規(guī)定3米以下的市政設施均應(yīng)粉刷防(fáng)護性塗料(liào)。電線杆、牌匾、雕塑等(děng)鋼結(jié)構表麵有了“保護膜”,一口氣就能吹掉上麵的小廣告。但是,這個規範難以落地——公共設施數(shù)量大、塗料費用高。
原北京市市政市容委曾統計,1張小廣告的成本不到(dào)0.1元,但清理成本卻達0.68元。北京主要路段清理一公裏每年就要花費約1.36萬元,僅西城區一年投入就要1300萬元。
麵對(duì)小廣告,人們很長一段時間(jiān)是束手無策的。它(tā)們(men)鋪天蓋(gài)地(dì),今天鏟了,明天就像野草一樣又重新出現(xiàn)。在清理和(hé)粘(zhān)貼的反複(fù)拉鋸中(zhōng),最後受(shòu)傷(shāng)的(de)是那些公(gōng)共設施——小廣(guǎng)告與金屬防腐漆一起脫落,逐漸生出紅褐色鐵鏽;為蓋住印章小廣告刷下的白漆,像極了一塊又一塊補丁。
社會管理學者王力(lì)一(yī)直關注小廣告(gào)治(zhì)理問題,曾出版《一(yī)指纏——“老剪報”杠上小廣告》一書,他將小廣告泛濫的原因歸結於(yú)“需求”。改(gǎi)革開(kāi)放使(shǐ)人們生活水(shuǐ)平提高,以前開鎖、通下(xià)水道隻能(néng)自己完成(chéng),後來都可以花錢雇人做。社(shè)會化分工解決了生活(huó)中部分難題,也帶來了城市病。登(dēng)不起廣告的人,想出小廣告的方法來增(zēng)加客源。“破窗效應”之下,眾人皆效(xiào)仿。
但低成本也成了違規(guī)、甚至違法行為的溫床,那些小廣(guǎng)告上的電(diàn)話號碼,通向的不僅僅是生活服務,也可能是一個個精心設計的陷阱(jǐng)。
當(dāng)時的懲處力度並不小。2002年,適用新的《北京市市容環境衛生條例》,東城區城管大隊搗毀一個散發百萬(wàn)張小廣告的公司(sī),一次性開出一萬(wàn)元的罰單。2014年,北京警方啟動(dòng)打擊整治非法小廣告專項行動,並在30天內共查獲非法(fǎ)小廣告(gào)違法人員4000餘人,收繳非法小廣告41.2萬餘張。2016年(nián),北京向組織(zhī)散(sàn)發小廣告的房地產企(qǐ)業開出40萬元罰單,創(chuàng)了北京城管執法部門針對非法小廣告罰款的最高紀錄。
可是張貼小廣告帶來的收益也很大。張貼小廣告的日薪從(cóng)每天20元到200元不等,一些不懂(dǒng)事的學生(shēng),把它當(dāng)為勤(qín)工儉(jiǎn)學。2006年時,有人靠貼(tiē)小廣告收入超過10萬元。那一年(nián),北京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2萬元。
合力
對於裴延印來說,在漫長的(de)28年裏很多時間(jiān)點已經模糊了,但是2008年一定是個節點(diǎn)。那一年,北京舉辦奧運會。世界的注視(shì),使得治理“城市牛皮癬”這件“小事(shì)”變得要緊起來。
也是那幾(jǐ)年,在各(gè)個區、街道、社區的宣傳下,手拿小鏟的形象幾乎成(chéng)為了這座城市老人世界裏的一股“潮流”。
這股潮流(liú)蔓延到大大小小的社區,居民們用小(xiǎo)鏟刀(dāo)對抗牛皮癬,有人把裝修剩下的洋灰拾掇起來,攢一(yī)堆兒,拿水(shuǐ)稀釋成糊(hú)糊,往牆上一刷(shuā)。等幹透了,小廣告(gào)就(jiù)能翹起來。
在天安門(mén)地區城管局工(gōng)作過的資深隊員韓東(化名)回憶說,小廣告最泛濫的那幾年,他(tā)負責的區域每個路口都(dōu)有十(shí)多個小廣告發放(fàng)者,他(tā)們站成一排往(wǎng)遊客手裏硬塞,環衛工人前腳掃了,後(hòu)腳遊(yóu)客又扔了。就(jiù)別提貼在地上(shàng)和指路牌上的,光是收集過往遊客手中的(de)小廣告,一米多高的大袋子,一天就能裝四五袋。
“北京是全國的門臉,他們這就是往臉的(de)鼻子尖兒上貼(tiē)。”韓東說(shuō),那時(shí),天安門地區城管局的工(gōng)作裏,清理小廣告的任務占到了60%。
在這場長期的貓鼠遊戲中,雙方關係變得微妙起來。他們既是陌生人,也是“熟人”。
和小廣告打交道多(duō)了,韓東(dōng)甚至一眼能看出哪個號碼經常(cháng)出現。有時正碰上(shàng)他們散發,韓東支起傘遮住臉,大步走過去,一抓一個準。有的人向他求饒,第二天又被逮到。久而久之,貼小廣告的人看(kàn)走路姿勢都能認出他來,狂奔到100米外還扭頭衝他笑。
有一段時間,裴延印和貼小廣告的人達成一種奇怪的“默契”——每天下(xià)午(wǔ)4點,有幾個年輕人會(huì)在(zài)立交橋下等(děng)他,等監督的人走了,橋下樹坑裏多了個垃圾袋,裏麵密密麻麻都是(shì)沒貼(tiē)的小廣告。
在裴延印眼裏,貼這些小廣告的年輕(qīng)人幾(jǐ)乎是他兒孫輩的孩子(zǐ),他盡量不與他(tā)們爭執,隻希望教(jiāo)育兩句,引他(tā)們走向(xiàng)正路(lù)。
韓東也(yě)有很多無奈。很多小廣告(gào)散發者都是些遊手好閑的(de)“小年(nián)輕”,從全國各地漂(piāo)到了北京,晚上(shàng)住橋洞,在公廁洗澡(zǎo),白天就出來發(fā)傳單(dān)、貼(tiē)小廣告。韓東查處過年齡最小(xiǎo)的小廣告散(sàn)發者(zhě)隻(zhī)有6歲。
年輕的隊員經常被他們問蒙(méng),“發小廣告違法嗎?我沒錢掙,得吃飯(fàn)啊(ā)!”
小廣告與社(shè)會問題糾纏在一起,使(shǐ)得本就一團亂麻的治理難(nán)上加難。
戰鬥
清理小廣告和貼小廣(guǎng)告的鬥(dòu)爭,大部分時候像是在遊擊戰,有(yǒu)時也(yě)會正麵遭遇。
裴延印記得,2012年的一段時間,他一連幾天都看(kàn)到,自己前一天鏟掉的地方,第二天又貼了一張一模一(yī)樣的小廣告。後來有天他特意(yì)晚出去半個小時(shí),看到年輕人嫻熟地將膠水(shuǐ)擠到小廣告背麵,“啪(pā)”一下(xià)摁到了電線杆(gǎn)上。
年輕人貼一張,他就撕一張。
“你是不是(shì)沒有(yǒu)錢(qián)吃飯了?揭廣告多少錢一斤?”年輕人質問道。
“我不缺這(zhè)點錢。別人(rén)往你臉上貼一塊破(pò)紙,你願意嗎?”老爺子教育他。
年輕人不聽這一套(tào),威脅明天再看到他揭小廣告,就把(bǎ)他的小(xiǎo)狗摔死。爭(zhēng)執之下,他向裴延印揮了一拳。裴延印閃(shǎn)了過去,眼看衝(chōng)突就要升級,附近巡邏(luó)的城管隊員趕來,年輕(qīng)人才尋機溜走。
裴延印是幸運的。這樣的威脅恐嚇在(zài)那個時期並不(bú)少。有人惱羞成怒,在小廣告上(shàng)詛咒“老太太撕一張少活一天”,有人衝(chōng)著16歲的醫院保安刺5刀,刀傷(shāng)離心髒隻有幾厘米。
直至2013年,一(yī)名57歲環衛工因清理小廣(guǎng)告被毆打致頭部縫針,再次(cì)引發眾怒。
如今,“城市牛皮癬”已經就要成為(wéi)一個被寫(xiě)進曆(lì)史的詞語。與小廣告張貼者鬥智鬥勇的(de)日子逐漸遠去。金大鈞圍著社區裏286棵老槐樹轉,看不到一張亂貼的小廣(guǎng)告。 但(dàn)裴延印還沒有停下來,他要繼續追擊“窮寇”。9月25日上午9點,他和老伴何秋蘭提著買來的蔬(shū)菜和鏟下的“戰利品”溜達回家。小(xiǎo)區周(zhōu)圍零散的(de)小廣告早已被他(tā)們清除一(yī)空。 時間走(zǒu)過28年,堅持(chí)下來的動(dòng)力不隻是閑來無事的(de)排遣(qiǎn),更像(xiàng)是一種“癮”。回味起那些與貼小(xiǎo)廣告者較勁的日(rì)子,成就感不僅來自(zì)城市(shì)變幹淨了,也來自一次次收獲戰利品時(shí)的滿足。 沒有人統計過他們倆鏟除的小廣告,但是少說也有(yǒu)幾百萬張。不光自己撕,他們(men)還帶動著221廠以前的老同事們一起撕。 工作過半輩子的基地住進了藏族同胞,他們邀請裴(péi)延印與何秋蘭回去看看,老兩口推脫了(le)好幾次——他(tā)們是社區裏五六個誌願組織的(de)骨幹力(lì)量,沒空出去玩。 記者 郭懿萌 編輯 楊海 校對 劉軍(jun1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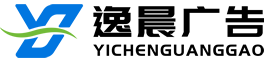
 當前位置:
當前位置: